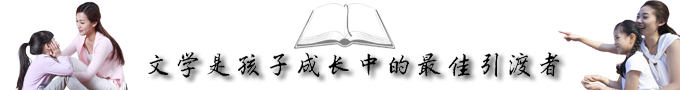长篇纪实散文《我爱我父母》第31章
来源:中国儿童文学网 作者:王泉滔
第31章
父母就我一个孩子,比着同龄的农家孩子,吃红薯饭食相对少点,但也没少吃。红薯是那个时代的主演,也是那个时代的宠物。那个年代人人都没少吃,我也没少吃。所以我对红薯情有独钟,有着诸多它的故事,如果不单独写写红薯,故事就此结束,我自己感到不够圆满,好像缺点啥,甚至有遗憾感。
社会进步,经济发展,是历史的必然。我读高中时,老师讲解一同学的作文,借题议论道:“解放前吃柳叶是为了活命,现在人吃柳叶是生活的点缀。”红薯也是这种转型,当代人吃红薯不仅是点缀,而且是享受。物以稀为贵,何况食物要多样化呢。
红薯有春红薯和麦茬红薯之分。春红薯要削成片,晒干储存起来;麦茬红薯又称秋红薯,一般不削成片,都是囫囵窖藏起来。
先说麦茬红薯。麦茬红薯收的比较晚,都是下了苦霜才收。不下大霜,红薯长不饱满,长不瓷实,里面的面粉津液缩不成蛋,吃起来不爽口,味寡涩,必须下了苦霜,把红薯叶打枯萎,绿色鲜嫩的叶子变成深褐色,甚至变成黑色,这个时候才是出麦茬红薯的最佳时节。太晚,红薯要冻烂地里,吃起来有酸苦头。
出麦茬红薯是有讲究的,不能一次把一大块地的秧子都割净,要先割一小片,把红薯从土壤里出出来,再割一小片,再把红薯出出来,循序渐进,最后把整块地里红薯都出完。要是一气把整块地的秧子都割净,土壤里的红薯一白天出不完,夜间的苦霜有可能把露头青打坏,以至于整个红薯很快都要坏掉。红薯有完全埋在地下的,有上半部露在地表外的,庄稼人叫这种红薯为“露头青”。庄稼人常年和地打交道,虽不能背诵《四书》《五经》,但对侍弄庄稼也是满腹经纶,而且形容事物很准。就说露在地表的红薯,庄稼人叫露头青,真是在贴切不过了,凡是露在地皮的部分都是青色的,一般是块大肥硕土壤包不住它才露出地面,是这些红薯的特色。所以,庄稼人形容那个人不听话,爱打别,处处都戗着茬,就称这种人为“露头青”。
不过有些不争气的红薯出出来,有意放在地里让霜打,霜打日头晒,锤炼几天,然后放地锅里一烀,稀溜好吃得无法形容。我那么小,也能吃一两碗。
那时出红薯还是原始的农具——抓钩。抓钩是出红薯的主要工具。因为用牛拉犁子出红薯,牛蹄、人脚加上犁铧的切割会坏掉很多,唯独人工用抓钩出出来的红薯才最毫发无损,完整干净,容易窖藏。
红薯出了窝,要把蒂和须去掉,所有不带伤的红薯都要下窖储藏,受伤的红薯要另外处理,或削成片,或打成粉,或喂牲口。喂牲口往往是舍不得的,几乎是打成粉。
浑身无伤的红薯要窖藏起来,窖藏好了,到第二年的麦季红薯就不带坏的。
窖,有酒窖、冰窖、地窖,储藏红薯的叫红薯窖。红薯窖不需要太豪华,也不需要多大的建筑,找一个空旷的地方,一般都选在河岸、沟边、树林等僻静处。根据红薯的多少挖一个长方形的地窖,也不能过分的大,一个地窖储藏红薯太多,容易坏掉。坏掉的红薯还有一个特点,一个坏掉,周围的红薯很快就要传染,发现晚了,一地窖红薯就完蛋了。
小时候跟着父母就是图新鲜、好玩儿,根本就不是干活儿。母亲在家做饭,我和父亲去刨地窖,地窖就选在村东南角的树林边。父亲用铁锨画了个痕迹,就一锨接一锨地挖起来。挖地窖没有一气挖好的,需要一上午或一天的功夫,要是不急用,两三天完成也不迟。把地窖挖好,上边还得封上顶,和盖房子差不多。先用棍梁固定好,再放上秫秸,最后封上土,一定留个进出地窖的门口。万物都是一理,和人居住的道理一样,这个“门口”要留南边。
地窖挖好后,就要把红薯从地里运回这里,一筺一筐地下到地窖里。红薯下窖很麻烦,也是个气力活儿,也是个技术活儿,红薯摆放不科学容易坏掉,科学来源于继承和经验。记得很清楚,父母储藏红薯的技术还是很好的,可以吃到年后的春天也不会坏的。
人不愧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,有着最高的智慧,吃穿住行处理得都头头是道。就说红薯吧,前面说了秋红薯的储藏,咱再来说说春红薯的制作吧。
秋红薯又称麦茬红薯,即割完麦秧后移栽,春红薯多于清明后莳秧,兹时已无霜降。很显然,种得早,自然成熟就早。红薯成熟不叫收,乡下人叫出红薯。出红薯在早,也得到了秋天,土地耕耘松软,小麦播种地下,麦芽钻出土壤,这个时候才是出春红薯的最佳时节。
因了还无苦霜,出春红薯不像秋红薯那样谨小慎微,一块地,一气出完,拾掇干净,过了秤,分成堆,按人口工分分到每家每户,这些红薯都是削成片的,窖藏不得。人擓车拉,把红薯分散到麦地里,再分成小堆,用专用工具削成片。这种工具家乡人叫红薯削子,一把类似镰刀的长方形刀片固定在木板上,刀片下有个洞,一人拿个红薯在削子上一来一回地滑动,红薯片很有节奏的一个接着一个诞生出来,不一会儿,红薯堆没有了,红薯变成了红薯片。
红薯片再散开,一片一个位置,不要两片叠加一起,这样耽误红薯片的晾晒,一旦遇雨就麻烦了。红薯片散开后成了雪白的银鱼,在阳光下好像在游动,发出耀眼的光芒,煞是壮观。
削红薯片忌讳太薄或太厚。太薄,太阳一晒就碎了,就抛糟了,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又沤在地里,庄稼人会心痛的;太厚,不易晒干,遇到雨,薄厚适度的红薯片晒干了,收回粮茓里,太厚的就要发霉,即便不发霉,太厚的吃起来也不好吃。
削红薯片还有个最大的危险,不小心铁削子会把手划破的,甚至能把手指割掉。那个时期的人,削红薯片没有几个人不被铁削子割破手的。有一次,母亲为了早一点把红薯消成片,速度快了些,不小心把手指割破了,鲜血淋漓,滴在白花花的红薯片上。母亲没有停止干活儿,简单地用粗布条缠绕几下,又继续干起活来,即便现在我当了医生,回想起来,心里还瘆得慌。
晒红薯片,最大的心愿就是不要遇到雨,在红薯片没晒干之前,一旦遇到雨就麻烦大了。退一步说,遇雨不怕,大小也不怕,就怕连阴天,这样红薯片一定会坏或霉在地里。所以,晒红薯片,天气成了农民最关心的事情。那时信息不发达,想知道天气的情况,就得和人打听,或者跟风走,看大家把红薯削成片,你也跟风,把红薯削成片。记得很清楚,三叔有个长江牌收音机,到了播放天气预报的时间,全村的人都去听,听了全国的,又听全省的。村民的经验说,全国听合肥,不听郑州,豫东虽属河南,雨水的降落和合肥跟拍,合肥下雨豫东就下雨,郑州不准。那时周口好像没名气,很少提及,村里人都是听许昌以南,说许昌以南的天气比合肥的更准。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:“南阳、信阳、驻马店中到大雨。”大人们问:“南阳、信阳、驻马店为什么最好下雨?”以至于后来我到了这三个地方,有意站在附近的最高处,看了看四周的景物,嗅了嗅这里的空气,尽管是窥其一斑,也算是对我记忆的补赏吧。
人算永远不胜天算,人算天有可能要被天否定。有一年晒红薯片,天气预报说没雨,还一连几天都是晴天,社员们都很高兴,连夜把红薯削成片。谁知天刚蒙蒙亮,雨就落了,而且几天不晴,雨落在地里,也落在农民的心里,地里霉了红薯片,心里霉了半年的希望。
说实话,人是要感谢天地的,没有天的恩赐,没有地的厚德,人不可能活得这么自在,吃霉红薯片毕竟是少数,应该是天地和人偶尔开次玩笑,怕人不敬畏天地了,让人永远记住天的崇高、地的伟大。在我的记忆里,霉红薯片都是父母吃,父母向来不让我吃霉变的食物。
从我记事起,红薯是人的主要食物,吃红薯和红薯变成的食物,大概有十几年,后来红薯变成了附加食品。我上了初中,红薯还是主要农作物,和父母一起栽红薯、浇红薯、翻秧、出红薯、削红薯、摊红薯片。所谓摊,就是把红薯片一个挨着一个地散开去,既不能拥挤,也不能太松散。太拥挤,不利于通风透气,就干得慢;太松散,浪费了地,拾起来也误时。等到红薯片被光和风烘得干了,瓦楞起来,就可以收回家,藏在茓子里,这就是一家人一年的主要粮食。所以,我很感谢红薯对人们的奉献,也感谢红薯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年龄再小一些,我对红薯就没有太多的记忆了。母亲提到一件事,又让我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。
父母把我家的红薯削成片,晒干后,还得一个一个地拾到筺里,然后运回家。那时农村人都很穷,有架子车的人家几乎没有。荆条编成的大筺叫它抬筺,小筺叫条子筺或箩头或篮子或畚箕,先拾到小筺里,再捯在抬筺里,等满了,就抬回家。父母就是用的这种抬筺把红薯片抬回家的。
抬筺很大,拾满一抬筺需要很多功夫。我很小,当然也记事了,父母蹲在月亮地上拾红薯片,我孱弱,就睡在父母不远处。父母给我铺个席,我睡在被褥里,虽是深秋,也没觉得太冷。满地的人影在挪动,满地的风在飘动,满地的月光在散发着清香。我趴在被窝里,贴着地表看麦苗前合后仰,也向远处的坟茔瞄了几眼,看有没有人们常说的鬼影。仰望天上的星星和月亮,产生很多奇妙的遐想。
父母拾满一抬筺,把扁担羁在襻子上,再把我抱在抬筺里红薯片上。父母抬起筺,也抬起我,悠悠地往家走去,这样一趟接着一趟,直把粮食归仓。至今想来,我不愿长大,并不是我不愿为父母分忧,也不是我不愿为家担当,而是我愿父母永远年轻、永远闪耀着青春年华的健康。
·上一篇文章:长篇纪实散文《我爱我父母》第32章:后记
·下一篇文章:风筝
转载请注明转载网址:
http://www.wpwx.cn/news/geyao/2257105974DJ85C8520HJD3FGDK68.htm
相关内容
|
王泉滔 |
|
王泉滔 |
|
王泉滔 |
|
王泉滔 |
|
王泉滔 |
|
王泉滔 |
|
王泉滔 |
|
王泉滔 |
|
王泉滔 |
|
王泉滔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