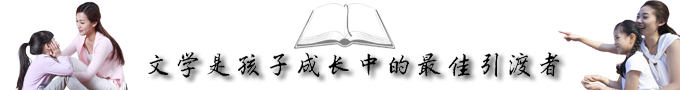村里的童年
来源:中国儿童文学网 作者:红玛瑙
二、“偷麦”挨打
上世纪70年代初期,住在村里的孩子是蛮快乐的。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学习负担一点都不重。因为没啥作业,孩子们可以玩的时间和花样都很多。跳皮筋、掷沙包、跳房子、抓骨头、抓石子等,应有尽有。男孩子的游戏就更多了。
村里的大场上(生产队最大的一块空地,麦收、秋收时作为队里的晒场,平时是集会的地方。)总有孩子在玩儿,男孩女孩都有,年龄不等。收麦子的时候,大场的孩子最多,往来穿梭到深夜。为什么呢?除了玩儿,这个时候来大场的孩子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,一个男女老少都心知肚明,又不愿意说穿的秘密——偷麦!
对!偷麦。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麦堆上假装玩一会儿。玩的时候,用双脚故意往下踩,让麦子灌满鞋子,然后抬起脚后跟,让鞋帮边的麦子溜到脚底,再把脚踏下去。踩实了以后,便假装回家一趟。
大约几分钟以后,这个孩子又会出现在麦堆上,重复刚才做过的事情。如此反复,有的孩子一晚上往来十几次,最多的能拿回家五六斤麦子。到夏收结束,有的孩子能偷生产队几十斤麦子呢。
生产队的干部就不制止吗?是的,他们不会制止。都是乡里乡亲的,再说,队干部的娃也在其中“忙”得不亦乐乎。
看着人家娃的行为,开始的时候,我不为所动,还挺看不起他们的。可是,看着满村的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偷麦,连一些大人也参与进来了,我的心开始动摇了。
看,旺财舅舅踮着脚尖回家了。瞧,彩棉妗子的裤腿怎么扎起来了?裤管里的麦子随着她走路,前后一摆一摆的,搞得她走路的姿势既别扭又滑稽。富贵表哥还跟彩棉妗子开玩笑,说:“彩棉娘,都不嫌麦芒扎腿啊?”
我在麦堆上玩的时间不短了。不用故意灌,鞋子里早已经装满了麦子。
我反反复复问自己:“该怎么办呢?把麦子拿回家不?”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个小时。我否定了再否定。到了大场的孩子越来越少的时候,我知道他们都跑累了,在完成最后一次“搬运”后,都回家睡觉了。
我也困了,也想回家睡觉了。可是鞋子里的麦子怎么办呢?往出倒吧?那会被所有的人看见。算了,还是带回家吧。反正别的孩子都如此这般“运”回家多少麦子了。
我也踮着脚、提着劲儿往家里走。心里“嘭嘭嘭”跳得越来越快。毕竟是偷麦,感觉全大场的眼睛都在盯着我看,第一次体会到“做贼心虚”的含义了。
与其说是走,不如说是挪。从大场到我家充其量有三分钟的路程,而我艰难地“走”了好长时间。进院子楼门时,我“咚”的一声摔倒在门槛上,膝盖磕得生疼。
母亲问我:“咋到这时候才回家?”
我说:“都在大场玩呢。”
停了一下,我邀功般地对母亲说:“妈,你来一下,拿个东西过来。”
母亲问:“咋啦?拿啥东西?”
我脱掉鞋子,倒出里面的麦粒,足足有两把。
母亲看见后,惊讶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。然后,她生气地对我说:“你怎么也做这种事啊?”
“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做,有的一晚上往他家偷了好多次呢,没人管!”我争辩道。
“人家的孩子我管不着,你就不行。人人都在做的事情不一定就跟着学。咱家再缺粮,也不要你这样!你要再去,小心我给你爸说。”
“好,我不去了。那……这麦子咋办?”我问母亲。
“丢到鸡棚喂鸡吧。”母亲极不情愿地回答了我。
这事以后,我没有再去大场。每天做完那一点点作业,就提着筐子给猪寻草。
一天下午,我正在河堤边寻猪草时,看见英红表姐蹲在生产队的麦地里。那一大片麦子还没有收割,英红姐蹲在麦子中,只有半个脑袋露出来。我以为她在蹲坑,心想:“英红姐也真是,十几岁的女子了,还在野外拉屎尿尿,难为情不?”
过了好一会儿,英红姐还不出来。我好奇地向她走去,喊着:“英红姐,你拉井绳呢?”
“玛瑙,你来,过来!快!”英红姐叫我。
我快步走过去,拨开麦子,来到英红姐面前。读者朋友们,猜猜我看见啥了?英红姐蹲在地里,用刀片割下麦穗,当场捋下麦粒,直接装进一个布袋子里。袋子里应该有七八斤麦粒了。
“英红姐,你胆子太大了!你都不怕人看见啊?”我问。
“谁管呢?人都在大场扬麦呢。你来,我给你割些麦穗,你捋一下,把麦粒拿回家就行了。”
“我不敢!我妈说我呢。”
“没事,你拿的多了,你妈就不说你了。放心,来,我给你割,你自己捋。”
我犹豫了好一会儿,最后还是蹲下来,照着英红姐说的做了。
天黑了,我们该回家了。英红姐的布袋子里已经装满了。我捋的麦粒没法儿拿,因为我提的筐子是装猪草的,缝隙太大了。
“用你的衣服一包,天已经黑了,你穿里头的衣服没人看见。记着啊,把猪草放在上面。”英红姐机灵地帮我想办法、出主意。
也是,天黑了,没人看见。我又照英红姐的话做了。
我穿着里面的背心,用短袖包好麦粒,放在筐子底,上面盖上厚厚的猪草。
我惴惴不安地向家走去,脑子里闪现着各种说辞和父母亲可能会有的种种态度。
夸奖?绝不可能!父亲是军人出身,母亲虽然是家庭妇女,但明事理。他们二人绝不会夸奖自己孩子的偷窃行为。
责骂?很有可能。上次从大场用鞋子拿回家两把麦子,母亲都说我了,好在父亲不知道那件事。
我万万没想到的是——父亲见我天黑了还没有回家,正站在楼门口担心地张望呢。
我该如何过父亲这道关啊?!我筛糠般地走近父亲。父亲接过筐子,问我:“咋到这晚才回家?”
“遇到英红姐了,跟她……多寻了……一会儿……草。”我浑身抖得站不稳,上下牙碰得“咯咯”响,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。
“咦?今天的草咋这重的?”父亲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。
“里面有……麦粒,英红姐给我割的……队里的麦穗……捋的。”
我不打自招,想先入为主,强调麦粒不是我偷的,我只是顺从英红姐的“好意”。
父亲突然沉默了。他拿出我的短袖,打开,一斤左右的麦粒在父亲的手里哆嗦着。不知道是父亲气得发抖?还是那些麦粒也吓得打颤,我想肯定是前者。
只见父亲“唰——”一下把麦粒抛洒在院子,一巴掌抽在我脸上。我连忙用手去捂脸,手还没有到脸上,又觉屁股上挨了狠狠一脚。我一个爬扑摔在地上,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大声哭起来。
“还有脸哭?!一个女娃,学啥不好?学着偷东西!把那些麦粒捡起来,给我吃下去,一粒都不准剩!叫你知道带贼腥味的东西不好吃!”
我跪在地上,一边摸索着捡麦粒,一边往嘴里塞,一边“呜——呜”地哭着,哪里敢看麦粒上是不是粘了土或者鸡粪。家里的十几只鸡整天在院子跑,拉的到处都是。
哥哥弟弟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。母亲看不下去了,拿着扫把过来连麦粒带土扫到一块,一句话没敢说,用眼睛示意哥哥把我拉回屋子。
父亲怒气冲冲地瞪着我,呼呼地出着粗气,那目光恰似成千上万的麦芒扎得我疼了几十年。
第二天,母亲告诉我说英红姐给我割麦穗是为了堵我的嘴。
……
大学毕业以后,我回老家教书十年,英红姐的消息时不时传入耳朵。
在我的孩子已经上了幼儿园时,英红姐还是单身。母亲说:“你英红姐太厉害,连偷带摸的,男人见了都害怕。”
后来,经人撮合,英红姐嫁到外省了。听说男人有残疾,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村。
再后来,听人说英红姐利用国家给残疾人的政策,养狐狸、开砖厂、办养猪场,还以女企业家的形象上了当地的报纸和电视。
那年夏天,英红姐开着红色宝马回来,给她爸妈(上文提到的旺财舅舅和彩棉妗子)盖了一栋六层楼房。村里人羡慕得口水流了一地。
父亲出奇地平静,没有评说一句。可我心里难受了几个月。想想我,上本科,上研究生,兢兢业业地教书,潜下心来搞教研,又是发论文又是出论著,每月只挣几千块钱。凭啥她开宝马,我连宝来都买不起?凭啥?凭啥?
再后来,我调往省城教书,好多年没有英红姐的消息。
时间过得好快,转眼自己五十多岁了。前阵子,我回村里行人情,和村邻闲聊时,偶然听到英红姐的消息。英红姐后来嫌办企业挣钱慢,带着儿子女儿去西南搞传销,结果被抓了。因为她是传销组织的负责人,判了十年,儿子判了五年,女儿判了三年。彩棉妗子在听到消息的第三天吐了血,没有救过来。旺财舅舅在彩棉妗子的头七,从英红姐盖的六层楼顶,头朝下跳了下去。
我今年五十六了,英红姐比我大九岁,应该六十五了。
写到这里,我的眼前忽然又浮现出父亲那天晚上的目光。瞪了我四五十年的目光再也不那么凶巴巴了,反倒是由里到外溢出一种别样的温暖。
·上一篇文章:奇妙的森林探险
·下一篇文章:你玩个博士研究生出来看看
转载请注明转载网址:
http://www.wpwx.cn/news/gushi/2011920826JFG3I1H966DFF87HE03C.htm
相关内容
|
匡天龙 |
|
王本来 |
|
匡天龙 |
|
王林鑫 |
|
江晓粤 |
|
张汝卿 |
|
胡敏珑 |
|
佚名 |
|
佚名 |
|
佚名 |